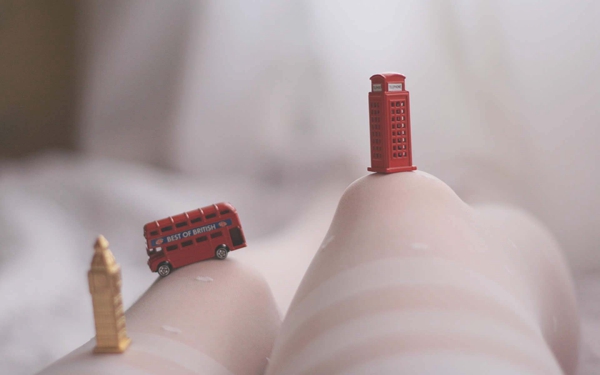岁月从一方手帕走过的心情日记
岁月从一方手帕走过的心情日记
在我儿时生活的那个小镇,手帕并不少见。当快开学时,在低矮的屋檐下,常见一些老妇人从斜襟衫的口袋里掏出手帕——那手帕的年岁恐怕和老妇差不多吧,又黑又脏,皱巴巴的,叠成巴掌大的方块;老妇人布满青筋的手将手帕掰开,小心翼翼地把包在里面的钞票拿出来,郑重地递给面前的孙子或孙女,语重心长叮嘱他们拿去交学费。
我小时家穷,家里买不起手帕用,由于哭了、感冒了流鼻涕,就习惯地用袖子往脸上、鼻端一抹,因此直到七八岁了,我所有的上衣袖子都仍油光发亮,硬巴巴地结成一块。念到初二了,没有洗脸巾,只能找条破得不能再穿的裤子,裁下裤腿代替。直到考上了高中,我才用得起手帕。
我买的手帕,最便宜的八分钱一块,三毛五的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新买的手帕往往舍不得用,像许多人一样,我将手帕叠成小四方形,平时只用上下两面;直到染上了不少污迹,才把崭新的里面翻出来,仍旧叠成小四方形,用脏了上面再用下面。
高中生已经懂得了臭美,在女生面前使用手帕,只能用来捂捂嘴、擦擦额角;如果要擤鼻涕,不能用手帕捂着鼻子擤,只能背着女生走到墙角,擤干净后,用手指将鼻涕星子挑起弹出窗外。因此,高中生的手帕不是用来揩脏东西的,而是用来掩饰有点脏的一面,衬托美的一面的。
我参加工作后一直用手帕,有了微小的变化——起初将手帕叠成斜三角形,斯斯文文掖在裤袋里,须用时再掏出来。但很快就不像高中生那样讲究,长胡子了,脾性也变粗了,在外干活满头大汗就更顾不得许多了,将手帕掏出来想也不想,就那么抹几下;在溪边、水龙头前洗了手,也用手帕抹几下。成家后养了女儿,小千金撒娇哭泣流了鼻涕,也用手帕抹几下;自己遇到挫折,遭受了打击,背着别人没有流泪,而是用手帕猛擂发酸的鼻端……
已婚男人的手帕,渐渐变得皱巴巴的,特脏,每周才洗一次,忙了、累了、忘了、懒惰了,说不定半月、一个月才洗一回。已婚男人的手帕最实用,最不讲究,最贱也最邋遢,常常邋遢过儿女的尿片。
已婚男人的手帕几乎完全丧失了掩饰功能,只能用于抹——抹掉脏,抹掉苦,抹落一张张日历;只能用来吸水——吸汗水和苦难的液汁,吸一天天的劳累,更深夜静时,吸几声沉重的叹息……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轰轰烈烈,陀螺似的忙,交际多了,一次在餐馆用餐,饭后我才第一次用上了餐巾纸,香水味儿幽幽地往鼻孔里沁。好闻吗?好闻。
渐渐地,我裤袋里的手帕失踪了;已婚的和还没成家的男人、女人的,还有老人和孩子的手帕,也统统失踪了,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餐巾纸。有湿水的,但绝大部分是干爽的那种,从五毛钱一小包渐次升级到八毛、一元,再到一元五毛、两元一小包。
某日闲暇,我拿出一小包餐巾纸凝视,一阵惆怅陡然从看不见的地方涌来,使我不禁鼻子一酸。这一酸之间——仿佛岁月跨过了二十年、三十年,脏兮兮的、厚厚的手帕,瞬间变成了洁白的、薄薄的一张餐巾纸,一下子托起了几代人的温馨。
岁月,真的从一方手帕上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