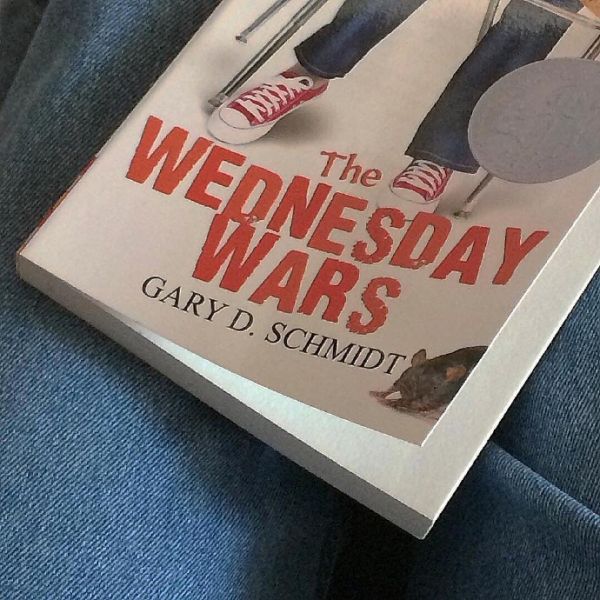新老制度经济学变迁理论比较研究
新老制度经济学变迁理论比较研究
新老制度经济学派由于哲学和方法论不同,从而对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属于不同的范式。本文从制度变迁的基本假设、层次与范围、主体和动力以及效率评价等五个方面比较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差异,旨在进一步理解历史和现实中的制度变迁现象。
一、导言 二、制度变迁的基本假定不同 老制度经济学所指的制度变迁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在假定制度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单项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研究,而是注重制度结构自身的历史性变迁。凡勃伦认为社会存在两大利益集团的对抗:一是思维习惯或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保守因素;二是受现存制度制约最大的从事工具性的职业集团,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因素,这样一种技术—制度或工具—仪式的二分法形成了凡勃伦传统。随后,艾尔斯和布什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包括两个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价值体系:工具价值与仪式价值。所以,老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可以看成是(即制度结构内部两种价值的冲突)凡勃伦—艾尔斯传统的技术二分法。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得的利润。通俗地讲,主体想从制度A变为制度B,是因为这种利润存在于制度B之中。只要这种外部利润存在,就表明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即在不损害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至少还可以使一个人的处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使社会净收益增加。所谓帕累托改进,实质上是指现有资源的配置还有改进的潜力。由于外部利润不能在既有的制度结构中获取,因此要实现帕累托改进、要获取外部利润,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再安排(或制度创新)或者是制度A变为制度B,这种新的制度安排的目的就在于使显露在现存制度安排结构外面的利润内部化,以求达到帕雷托最佳状态。 三、制度变迁的层次与范围不同 新老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理解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从两派代表人物对制度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旧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制度无非是一种自然习俗,由于习惯化而被人广泛地接受;康芒斯则认为,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的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运营机构;艾尔斯把制度说成是以仪式行为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而仪式行为本身包含了社会习俗;当代最著名的老制度经济学家霍奇逊认为,制度是通过传统、习惯或法理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的行为类型的社会组织;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从约束人的行为规则这一角度来观察制度;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拉坦也认为,“一种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相互关系。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往往把制度看作是一种规则,尽管诺斯把制度分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倾向于把制度理解为正式规则,而老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理解成风俗、社会惯例乃至人们的思想习惯,这些很明显都存在于社会的非正式规则之中”。所以,相比较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大多数是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的更为具体层次的制度变迁,而老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含义更为广泛,试图分析和解释大范围基本层次的制度变迁。 四、制度变迁的主体界定不同 制度变迁的完成必须以人作为行动的主体,但是老制度经济学中,这一主体究竟是谁始终是模糊的。凡勃伦把普通大众和工程师视为这一主体,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他们却无法行动,因为凡勃伦反对暴力革命,希望借助于技术自身的发展来完成制度变迁,这种原理又被后来布什的仪式锁闭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仪式锁闭否定技术行为模式突破仪式行为模式的支配可能性。进步的制度变迁是通过既得利益集团中的精英,有意识地引进有利于自己的技术进步来实现的。既然在现存社会结构中可能的技术进步要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允许,那么技术进步就始终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进步的制度变迁就不会发生,所以维护自己利益的精英不可能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总而言之,在老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变迁的主体始终是不明确的,或者说是缺位的,即使有也是与其理论本身相矛盾的。而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明确的,主要包括政府、团体、个人。但是,三者本质都一样,都是为了从创新中获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强制性变迁模型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由于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国家在制度供给的生产上具有规模经济,主要在于统治者需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诺斯借鉴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认为,广义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重要主体。在稀缺经济下的竞争导致企业家加紧学习以求生存,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潜在利润,从而进行制度创新。在分析制度变迁的过程时,诺斯还将制度变迁的主体区分为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初级行动团体是一个决策单位,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变迁的进程。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都是某种特定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次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具体实施者,他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而进行制度变迁的团体。初级行动团体能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入,而次级行动团体不创造收入,只参加收入的再分配过程。因此,这两级行动团体的关系可能是一群制度变迁主体之间的主从分工,也可能是一个变迁主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主从分工,因为一项制度的变迁往往需要多个主体协作才能完成。 五、制度变迁的动力不同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追求制度变迁的收益。因为新制度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分析的框架来研究制度变迁,它只能从单个制度变迁主体的行为动机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主体都是财富最大化者,他们从事制度变迁都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只有当制度变迁有利可图时才会发动创新。舒尔茨分析了由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导致对有关制度需求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均衡,从而有了创新的机会,这实际上是说明相对价格变化导致制度变迁。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明确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他创造了建立更有效的制度激励,似乎一切受到激励的制度变迁都是有效的。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政府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并基于自身的成本-收益来推动制度变迁的。而在旧制度经济学看来,技术进步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因为根据凡勃伦—艾尔斯传统的技术仪式二分法,仪式体系是保护权威的保守力量,只有技术是动态的不断前进的。正如艾尔斯所说:“人类历史充满了这两种力量持续不断的冲突,技术的动态力量不断发生变化,而仪式这种静态力量……对抗变迁。”凡勃伦也坚持认为,技术进步决定制度变迁。他认为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具有保守的倾向,而技术是不断变化的,技术决定制度,制度必须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凡伯伦把制度变迁的希望寄托在代表着先进技术要求的普通大众或者工程师身上;艾尔斯提出“技术决定原则”,而布什强调进步的制度变迁需要技术动力。 六、制度变迁的方向与效率评价不同 凡勃伦从达尔文那里吸收了进化思想作为他的基本方法,所以他反对正统经济学的目的论和功利主义哲学。他认为,社会应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这个过程是进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没有特定目的的持续的“方向飘移”过程。制度变迁既可以表现为进步,也可以表现为退步,制度变迁没有方向。所以,在旧制度经济学看来,评价制度变迁的效率不是经济效率,由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范畴,他们关注的不是制度的绩效,他们用价值原则来评价制度变迁。凡勃伦认为,衡量制度变迁好与坏的标准是:“生命的便利程度,也就是延续和改善人类的生命过程。”只要提高了整体的生活便利程度,就是进步的制度变迁。艾尔斯也认为,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生命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从而有利于生命过程的延续。总之,旧制度变迁关注的价值不是个人价值,而是社会价值。价值标准是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和生命过程的连续性联系在一起的,应该从是否有利于人类生命的连续性和共同体的重构,而不是从全体的基础出发来评价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对于新制度变迁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种功能倾向,即将制度变迁的经济功能放在核心地位,其本质是一种构建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的方向很明确,似乎任何一项制度变迁都是人类经过理性计算的结果,都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所以对制度变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比较是评价的主要方法。布罗姆利从供需方收入的角度出发认为,“当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时,制度供给者就会致力于制度创新,因此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一个可采取的分析是看一看变迁的潜在收益是否能补偿那些源于这种变迁的损失。”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所以对制度变迁的效率主要关注经济效率,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大产出。 七、结语 尽管前文已经评价了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差异,但它们之间还是在许多方面存在可沟通性之处,两种制度变迁理论之间存在互补的可能性。“确切地说,可以在比通常认识到的还要大得多的范围内互相对话,这样的对话可能会有重大收获,尤其当面临的问题的相似性以及所存在的互补领域成为讨论的焦点时”。所以说,两种理论在对制度变迁的解释上是可以互相结合的,在制度变迁的层次上,既要看到正式制度变迁,又要看到非正式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动力上,既要看到相对价格的变化,又要看到技术进步的推动;在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上,既要关注经济效率,又要关注人类生命的发展质量。只有如此,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历史和现实中的制度变迁现象。诺斯后期著作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注重以及研究思路与老制度经济学派极为相似,诺斯的这一“改弦更张”使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互相结合看到了希望。